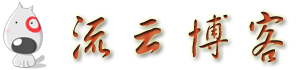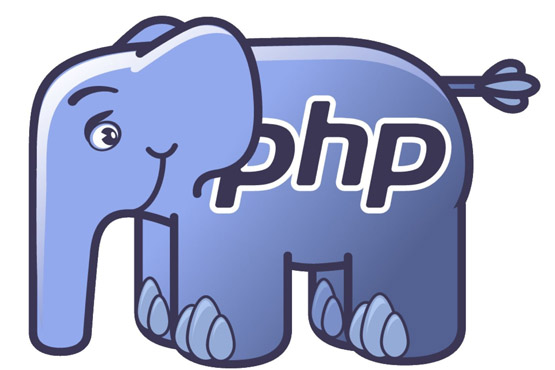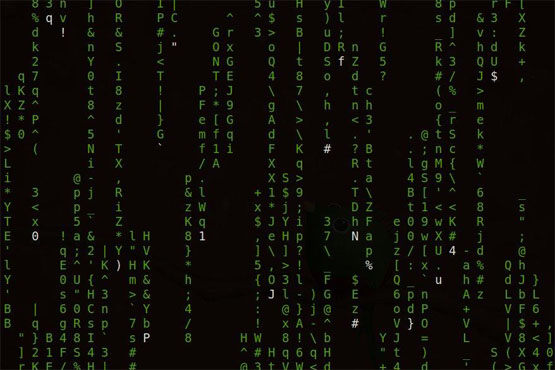一日,人民路的路灯亮起暖黄的光,阿秀抱着吉他坐在街角的石阶上,沈复站在她身旁,手中握着一支中性笔 —— 这是阿秀给他的,说比毛笔方便,他琢磨了半天才学会怎么用。
沈复听得入神,等她唱完,提笔在便签纸上写下:“洱水映月照归舟,清风伴我解烦忧。苍山雪落沾衣袖,此心安处是温柔。”
阿秀接过便签纸,看着遒劲的字迹,眼睛亮得像星星:“这几句太妙了!正好能接在我唱的后面!” 她调整了一下琴弦,重新开口,先唱自己的歌词,再接沈复写的诗句,歌声与诗词交织,像溪水绕着山石流淌,格外动听。
那晚,阿秀的吉他包中多了不少零钱,还有人问她:“你身边这位‘古装公子’是哪里来的?诗写得真好!” 阿秀笑着说:“他是我的朋友,沈复,特别有才华。”
之后的日子,沈复每天都跟着阿秀。清晨,他们去洱海畔看日出,沈复踩着湖边的鹅卵石,看着朝阳从苍山后跳出来,把湖水染成金色,忍不住感叹:“此景堪比太湖晨雾,却更显壮阔。若芸娘在此,定会折枝杜鹃插在鬓边。” 阿秀听他提起 “芸娘”,知道是他的妻子,便轻声说:“等下次遇到杜鹃花,我们采些晒干,做成书签,也算替芸娘留个念想。”
阿秀教他用手机扫码付款,第一次在早餐铺买豆浆时,沈复对着二维码扫了半天,手都在抖,生怕扫错了 “咒语”。阿秀还教他骑共享单车,他一开始总怕摔下来,双手紧紧抓着车把,身子绷得笔直,阿秀在旁边扶着车后座,笑得直不起腰:“沈公子,你放松点,这车子很稳的!”
午后,他们去喜洲古镇逛,沈复对着白族民居的 “三坊一照壁” 惊叹不已:“这榫卯工艺竟与江南不同,不用一根钉子,却能支撑百年,古人的智慧当真了不起。” 阿秀带他去看白族老奶奶做扎染,蓝色的染料在白布上晕开,像苍山的云。沈复伸手摸了摸染好的布,说:“明代也有扎染,叫‘绞缬’,只是颜色多为青、褐,这般鲜亮的蓝色,倒是少见。” 老奶奶听了,笑着说:“小伙子懂行啊!这是用板蓝根做的染料,咱们大理的扎染,可是非遗呢!”
傍晚,他们去苍山徒步,沈复穿着阿秀给他买的棉麻外套,比长衫轻便多了。走到半山腰时,遇到一群卖野蜂蜜的山民,沈复尝了一口,说:“这蜜比苏州的枣花蜜更清甜,带着草木香。” 山民说:“这是苍山的野杜鹃蜜,一年只采一次。” 阿秀买了一小罐,说要回去给沈复泡蜂蜜水。
沈复渐渐适应了现代生活,他学会用手机记笔记,把想到的诗句写在备忘录里;学会用导航,再也不会在古城里迷路;甚至学会了用洗衣机 —— 只是第一次用的时候,把长衫和阿秀的连衣裙一起放进去,结果长衫的墨色染到了连衣裙上,他愧疚了好几天,阿秀却笑着说:“没事,这裙子现在成‘扎染款’了,更特别。”
他也把《三白游记》的故事讲给阿秀听,讲他和芸娘在七夕拜天孙,讲他们在沧浪亭赏月,讲芸娘为他做 “活花屏”。每当这时,阿秀总会靠在他肩头,轻声说:“三白,芸娘一定是个特别温柔的人,你们的日子真浪漫。”
沈复望着远处的苍山,轻声说:“以前总觉得,失去芸娘后,我的人生就只剩下回忆了。可遇到你,来到大理,我才知道,人生还能有新的风景。”
这天,阿秀说要带沈复去一个 “好地方”。他们穿过人民路的小巷,来到一家挂着 “月明小筑” 招牌的酒馆前,门口摆着几盆三角梅,窗户里飘出激烈的音乐,还有人在唱歌,声音沙哑却有力量。
“这是老沙的酒馆,他以前是摇滚歌手,唱歌特别好听。” 阿秀推开门,音乐瞬间涌了出来 —— 一个留着及肩长发的男人正抱着电吉他弹唱,他穿着黑色皮衣,牛仔裤上有破洞,脚下踩着一双马丁靴,每唱到高潮,台下的客人就跟着拍手叫好。
“老沙!” 阿秀挥手喊道。男人停下吉他,看向他们,脸上露出笑容:“阿秀来了!这位是?” 他的目光落在沈复身上,上下打量着他的棉麻外套,“你朋友?打扮挺复古啊。”
“他叫沈复,特别会写诗!” 阿秀拉着沈复走到台前,“老沙,你今天唱的这首《人生几何》,我上次听了就特别喜欢。”
老沙放下吉他,从吧台拿了两瓶啤酒,递了一瓶给沈复:“兄弟,先喝口酒,咱们慢慢聊。我叫老沙,你叫我沙哥就行。”
沈复接过啤酒,学着老沙的样子拧开瓶盖,抿了一口,苦味中带着麦香,比他以前喝的米酒烈多了。“沙兄,在下沈复,字三白。” 他拱手道,“方才听沙兄唱歌,歌词中满是自由之意,让人佩服。”
老沙笑了:“兄弟,你这说话方式挺特别啊!我这歌写的是我以前的日子 —— 年轻时组过乐队,叫‘风中追沙’,在全国各地巡演,每天不是在舞台上,就是在去舞台的路上。后来乐队散了,我就来大理开了这家酒馆,也算换种方式追求自由。”
沈复放下啤酒,轻声道:“沙兄这般洒脱,与某倒有几分相似。某以前在苏州,与妻子芸娘相依为命,不求富贵,只求能诗酒相伴。后来芸娘去了,某以为人生再无乐趣,直到来到大理,遇到阿秀,又认识沙兄,才知生活仍有盼头。”
老沙拍了拍他的肩膀:“兄弟,过去的事别总放在心上,活着就得往前看。你不是会写诗吗?我弹首曲子,你给配段诗,咱们合作一把,怎么样?”
沈复点头:“固所愿也,不敢请耳。”
老沙抱起电吉他,指尖划过琴弦,激烈的旋律瞬间填满酒馆 —— 不是刚才唱的《人生几何》,而是一首更舒缓的曲子,像苍山的云在慢慢飘。沈复闭上眼,想起这些日子在大理的经历:洱海的日出、喜洲的扎染、阿秀的笑容、老沙的歌声,还有对芸娘的思念。他张口念道:
“苍山雪落覆青巅,洱海月升映碧天。
偶遇佳人歌伴酒,相逢知己话当年。
浮生若梦何须叹,此世心安即故园。
且把新愁融旧曲,风吟雨唱醉人间。”
念白与旋律完美契合,台下的客人都安静下来,静静听着。等沈复念完,老沙弹完最后一个音符,酒馆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,有人喊:“再来一个!”
老沙笑着看向沈复:“兄弟,你这诗写得绝了!比我那些歌词有味道多了!以后你可得常来,咱们多合作几次。”
从那以后,沈复成了 “月明小筑” 的常客。每天晚上,阿秀在人民路唱完歌,就会和沈复一起去酒馆,老沙会留一瓶冰镇的啤酒给沈复,留一杯柠檬水给阿秀。
老沙教沈复弹吉他,沈复的手指灵活,以前弹过古琴,学吉他倒也快,没多久就能弹简单的旋律。沈复则教老沙写格律诗,老沙以前写歌词都是自由体,第一次写律诗,总把韵脚弄错,沈复就耐心教他:“平声韵脚要统一,比如‘天’‘年’‘园’‘间’,都是平声,读起来才顺口。”
有次老沙写了首《大理夜话》,开头是 “洱海边的风,吹了多少年,我在酒馆里,等一个春天”,沈复帮他改成:“洱海风吟数百年,酒馆灯暖待春还。吉他声里藏旧事,醉里高歌意自闲。” 老沙读了好几遍,拍着桌子说:“兄弟,你这一改,意境就出来了!”
他们还一起改编歌曲,把沈复写的诗谱成曲。有首《苍洱知己》,老沙弹吉他,阿秀唱副歌,沈复念诗,每次唱到 “相逢知己话当年”,台下的客人都会跟着拍手,有人还会举起手机录像,说要 “发抖音,让更多人知道大理有这么厉害的组合”。
老沙也给沈复讲他的过去:“以前在乐队时,我们去迷笛音乐节演出,台下有几万人,喊着我们的名字,那种感觉特别爽。可后来乐队因为理念不合散了,我消沉了好长时间,直到来大理,看到苍山洱海,才慢慢想通 —— 音乐不一定非要在大舞台上,在小酒馆里,能有人听我唱歌,能遇到你这样的知己,就够了。”
沈复听着,想起自己当年因家境贫寒,不能参加科举,只能靠卖画为生,却也从未放弃对文学的热爱。他举杯道:“沙兄,某在万历年间,虽有芸娘相伴,却少有能彻夜长谈的知己。如今遇你,实乃平生幸事。这杯酒,敬知己!”
老沙也举杯:“敬知己!敬大理!”
阿秀看着他们,笑着举起柠檬水:“我以水代酒,敬你们!也敬我们在大理的日子!”
月光透过酒馆的窗户洒进来,落在三人身上,吉他靠在墙角,啤酒瓶在桌上泛着光。沈复看着眼前的知己与挚友,又望向窗外的苍山剪影,心中忽然明白 —— 那场突如其来的穿越,或许是命运的馈赠。他虽远离了万历年间的江南,却在大理找到了新的归宿,找到了能与他共享苍山洱海、共赴诗酒年华的人。
转眼到了农历三月,大理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三月街。阿秀说,三月街是大理最热闹的节日,有赛马、对歌、摆摊的,能逛上一整天。
那天清晨,沈复、阿秀和老沙早早起床,老沙开着他的二手车,载着两人去三月街会场。路上,老沙说:“我第一次来三月街,看到赛马时,差点把手机掉进泥里,太刺激了!”
到了会场,沈复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:街上挤满了人,有穿白族服饰的老人,有背着背篓的妇人,还有像他们一样来游玩的游客。路边的摊位摆着各种东西:有卖药材的,当归、三七堆得像小山;有卖手工艺品的,木雕、竹编琳琅满目;还有卖小吃的,烤乳扇、炸洱海鱼的香味飘得老远。
“快看,赛马要开始了!” 阿秀拉着沈复往赛马场跑。赛道旁挤满了人,沈复踮着脚,看到几匹骏马从远处跑来,骑手们穿着彩色的衣服,身姿矫健。“这马跑得真快!” 他忍不住赞叹,“比苏州的驿马还快几分!” 老沙笑着说:“这些都是大理的矮脚马,别看个子不高,跑起来特别稳。”
看完赛马,他们去逛对歌台。有个白族老汉拿着三弦琴,唱着白族调:“苍山十九峰,峰峰有积雪,洱海十八弯,弯弯有渔船。” 台下有人跟着唱,阿秀也拉着沈复一起学,沈复学得慢,调子总跑,惹得阿秀和老沙笑个不停。
轮到游客对歌时,有人起哄让沈复唱。沈复也不怯场,清了清嗓子,用明代的调子唱道:“洱水泱泱映日红,苍山巍巍雪初融。三月街上人如织,相逢一笑意融融。”
他的歌声带着古风,与白族调截然不同,台下顿时安静下来,随即爆发出掌声。那个白族老汉走上前,握着沈复的手说:“小伙子唱得好!有文化!” 沈复笑着拱手:“老伯过奖了,某只是随口唱唱。”
逛到中午,他们找了个小吃摊坐下,点了烤乳扇、炸洱海鱼、酸辣粉。沈复第一次吃酸辣粉,辣得直冒汗,却停不下筷子:“此物又酸又辣,太过瘾了!比苏州的腌菜还够味!” 老沙递给他一瓶冰镇啤酒:“慢点吃,别噎着,喝点啤酒解辣。”
下午,他们去买药材。老沙说他母亲有风湿,想买点三七回去。沈复跟着老沙在药材摊前逛,帮他辨认药材:“这三七要看断面,断面呈灰绿色或黄绿色,有放射状纹理的才是好的。明代的《本草纲目》里有记载,三七能‘止血,散血,定痛’。” 摊主听了,笑着说:“这位兄弟懂行啊!我这三七都是自家种的,绝对正宗。”
买完药材,阿秀拉着他们去买扎染布。她看中一块蓝色的扎染裙,沈复帮她挑:“这块布的花纹像苍山的云,晕染得很自然,穿在你身上肯定好看。” 阿秀笑着买下,说要在下次唱歌时穿。
傍晚,他们满载而归。老沙开车时,阿秀哼着白天学的白族调,沈复靠在车窗边,看着夕阳把苍山染成金色,心中满是温暖。
大理不冷,却常有雨。有次下雨,沈复和阿秀没带伞,躲在 “月明小筑” 酒馆的屋檐下。老沙看到了,把他们拉进酒馆:“外面雨大,进来避避,我刚煮了姜茶。”
姜茶冒着热气,喝下去浑身暖和。老沙说:“过节了,你们往年今日在哪里?” 阿秀说:“我家在四川,不想回去,想在大理过。” 沈复沉默了 —— 他没有家可以回,万历年间的家,早已成了过往。
老沙看出他的心思,拍了拍他的肩膀:“三白,你要是不嫌弃,就跟我一起过节。咱们在酒馆煮火锅,再唱唱歌,也热闹。”
沈复看着老沙和阿秀,眼眶有些湿润:“多谢沙兄,多谢阿秀。有你们在,沈某就不再孤单了。”
他们煮了一大锅火锅,有洱海鱼、虾、青菜,还有老沙从四川买来的火锅底料。老沙弹吉他,唱《蝴蝶泉边》,阿秀跟着唱,沈复则用手机录下来,说要 “留作纪念”。
吃到一半,沈复起身,从怀中拿出一张纸 —— 是他写的《苍洱知己赋》,他轻声念道:“万历风絮,卷我至苍洱之滨;现代繁华,遇我之知己之人。阿秀善歌,声如洱海之月;老沙善乐,曲似苍山之风。三人相聚,把酒高歌,不问过往,只惜今朝。此乃浮生之幸,此生之欢……”
念完,老沙和阿秀都鼓起掌来。老沙举杯:“好一个‘此生之欢’!这杯酒,敬我们的友谊,敬大理!”
沈复和阿秀也举杯:“敬友谊!敬大理!”
窗外的雨停了,月亮从云层后探出来,照在酒馆的灯笼上,温暖而明亮。沈复看着眼前的知己,心中明白,无论他来自哪个时代,无论未来会怎样,只要有阿秀和老沙在,有苍山洱海在,这里就是他的家,就是他的 “此心安处”。
此后,每当有人问起沈复,他总会笑着说:“某乃沈复,字三白,来自万历,却愿在此生,与阿秀共赏苍山雪,与老沙同醉洱月酒。” 而大理的风,总会带着他的笑声与诗句,飘向洱海,飘向苍山,留在这方让他重获新生的土地上,成为一段跨越时空的知己佳话。